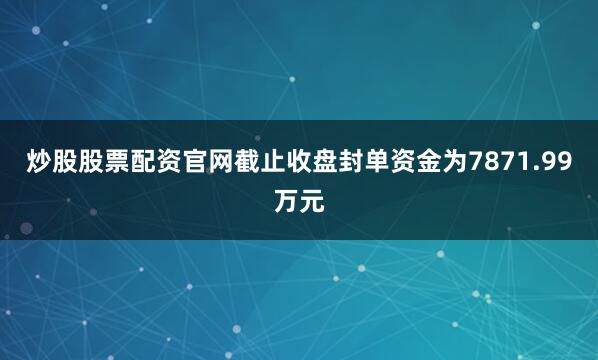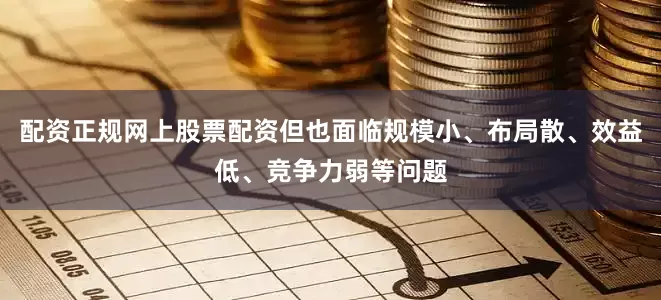亲爱的陌生人你好,我叫曙光。
一个曾被校园霸凌深深改变的女孩。
我本不是懦弱的性子,却在初中那段被针对、被孤立的时间里,学会了恐惧,学会了讨好。
我以为,等我逃离那个环境后,一切都会变好。
后来才发现:
那些我以为终会过去的伤害,就像看不见的藤蔓,在我的人生里悄然疯长,紧紧地缠住我,让我难以呼吸。
直到我选择直视它、斩断它,才得以挣脱。
如果你愿意,可以与我一同回顾我的“改变之路”。
希望这一段“路程”,也能给你带去一些力量和启发。

我似乎被囚禁在过去
初中刚入学时,我还是年级前三的“好学生”。
这成绩本应是“光环”,却成了其他人伤害我的“原罪”。
恶意,出现得莫名其妙。
初二时,新上任的班长小芸成绩中等,擅长交际。
有一次,她课间来问我问题,我因为先答应了同桌,就说晚点再跟她讲。
却不曾想,从那天起,隐形的霸凌开始了:
我的抽屉里总出现揉成团的草稿纸,上面写着“装什么好学生”;
上课时,我的课本总会突然“失踪”,文具这些,要用时也总找不到;
去食堂吃饭,我刚打好饭,起哄声就随之而来:“快给人好学生让座,耽误她吃饭,考不好就赖你们咯”……
这场“心理霸凌”持续到我初中毕业。
被孤立、被针对、被造谣——这些不是电视剧里的情节,而是我每天上学都要面对的状况。
我逐渐活成了一个卑微的“透明人”:
能不让别人注意到我,就尽可能“隐身”;
遇到可能发生的冲突,就主动道歉、拼命讨好,生怕引来更大的恶意。

等上了高中,我的生活才终于回归正常。
可敏感的神经早已根深蒂固:
我主动“占据”教室后排的角落,拼命减少自己的存在感;
上课时从不敢举手发言,一被老师叫起来声音就发抖;
也不敢跟谁亲近,生怕ta突然翻脸“捅”我一刀……
大学,我考到了离家1500公里远的城市,以为终于能彻底逃离。
却在开学不久的一次宿舍夜谈中重回“噩梦”:
那时,大家凑一起吐槽教官的过分严厉。
当小A的目光无意扫向我时,我慌乱挤出一句:“毕竟是军训……”
见她皱了下眉,就慌了神,往回“找补”:“但他确实太苛刻了!”
室友们没什么反应,继续激烈地吐槽着。
而我,却深陷在熟悉的、如坐针毡的感觉中。
我原以为,时间和距离能抚平伤害。
没想到,它早已刻进我的血肉,成了我面对冲突时无法自控的应激反应。
选择去心理咨询,是因为我暗恋的男生。
某天,他发消息约我去图书馆。
当邀请信息出现在我眼前时,恐慌瞬间攫住了我:
他是不是在开玩笑?他是不是和别人打了赌?他肯定会很快觉得我无趣、麻烦……
我颤抖着敲下拒绝的借口,然后丢开手机,在黑暗中蜷缩起来。
一种巨大的失落和自我厌弃沉沉压下:
我似乎永远被囚禁在过去的阴影里。
就连善意也会让我恐惧,生怕那是另一场风暴的前奏。
这是霸凌带给我的最深的印记——我自己成了内心那个永不疲倦的“刽子手”。

那一刻我意识到,我真的需要帮助。
带着强烈的想自救的心,我预约了人生中第一次心理咨询。

我的低头和讨好不是懦弱
第一次走进咨询室时,我慌得手心全是汗。
咨询师W的声音比想象中更温暖,“你愿意先说说,为什么今天来找我吗?”
我沉默了,心里做着斗争:“她会不会也伤害我?”
而这段时间里,W只是静静地,温柔地看着我,没有催促,没有不满。
我一咬牙,语无伦次地讲述那些压抑了许久的碎片:
初中的孤立无援,高中、大学也仍如影随形的恐惧,在人际交往中令人窒息的自我怀疑,以及那个日夜不休、指责“我不够好”的内在声音。
讲到最后,声音哽咽,几乎无法成句。
W就那样专注地听着,目光中没有任何评判。
当我终于艰难地描述完那种“无论怎么做都没用”的窒息感时,她轻声说:
“这听起来,很像心理学中说的‘习得性无助’。你初中时经历的那些孤立和挫败,一次次地浇灭了你对人际关系的信任和尝试改变的勇气。
久而久之,你的身体和心都‘学会’了:保持沉默、低头、讨好。这似乎是唯一安全的生存策略。”
这是我第一次听到,这个精准概括了我十几年状态的名词——习得性无助。
原来,我的不敢抬头和恐惧讨好,并不是因为我懦弱。
而是过去的痛苦经历在我身上刻下的烙印,是一种被迫学会的自我保护机制。

W拿出一张白纸,轻轻放到圆桌中间:“现在,让我们试着画一条线,代表你从初中到现在的时间轴。试着把那些让你特别痛、特别无力的点标记出来,比如初中那个被嘲讽包围的午休,比如大学那个你拒绝善意的瞬间……”
我犹豫着拿起笔,手微微发抖。
当那些痛苦的场景被具象化为纸上的一个点、一个叉时,一种奇异的感觉升起:
它们不再是不停吞噬我的迷雾,而是可以被看见、被定位的“事件”。
当伤口被清晰地标记在时间轴上,它便不再是扩散的阴影,而成了可以丈量和面对的过往。
“它们曾经伤害了你,”W的声音很轻,却带着一种坚定的力量,“但你看,走到了现在的你,比初中时的那个小女孩强大了多少?你可以用现在的力量,去理解、去保护过去的那个自己。”
接着,W递给我一个手掌大小的线圈本,“试试这个。从今天起,每天睡前写下:今天我做了什么让自己感觉‘我还不错’的事?或今天我有哪一刻,没有严厉地指责自己?哪怕只有一条,哪怕事情再小,都可以。”
起初,这件事对我来说无比艰难。
“今天,按时去上了早课(虽然还是很困)。”
这是我硬着头皮想了很久才写下的,又干巴,又满是自我怀疑。
可坚持一周后,微小但奇妙的体验发生了:
“今天小A分享零食,我自然地接过来吃了,没有像以前那样反复推拒、害怕欠人情。”
写下这行字时,一丝微弱却真实的暖意涌上我的心头。
原来微小的自我肯定,是照亮黑暗的第一根火柴。
它的光芒虽弱,却足以证明黑暗不会是永恒。


我不再用过去的痛苦惩罚自己
后来的咨询,探索到更深一步:
回溯过去,和W站在更高的视角,更加客观地捋清那段创伤。
W提出:“现在的我们有了更多的‘不错’,此刻的你也相对安全。有没有勇气,带着现在的理解和力量,一起回去看看初中那个最艰难的时刻,看看那个小小的你?”
我紧张地点点头。
在咨询室这个安全、包容的空间里,在W的引导下,我闭上眼睛,试着回到那个被嘲笑后孤立无援的课间。
但这一次,我有盟军了。
W的声音平稳:“你看到了吗?那个小小的你,缩在座位上,那么害怕,那么孤独。现在的你,想对那时的自己说些什么?”
我瞬间飙泪,过了很久,断断续续地说:“我想抱抱她。我想告诉她,不是她的错,她很好。错的是那些嘲笑她的人!她值得被好好对待……”
这些话带着压抑了太久的委屈和心疼冲出。
那一刻,跨越时光的拥抱终于完成。
那个小小的我,终于被保护了。
W告诉我:“这就是疗愈的开始。用此刻成年人的理解、悲悯和力量,去拥抱、安抚那个受伤的内在小孩。告诉她,你看见了她的痛苦,那不是她的错,她值得被爱。”
当现在的自己终于伸出手,温柔拥抱过去那个蜷缩在角落的孩子,真正的和解才从心底生根发芽。
改变是慢慢发生的。
当暗恋的男生又一次发出一起看展览的邀请时,熟悉的恐惧感袭来。
这次,我没有立刻回复。
而是深吸一口气,然后删删改改自己的信息,最终发出:
“上次很抱歉没法一起去。这次展览我也挺感兴趣的,要不周末去?”
然后,立刻把手机扣上,像在等待宣判。
几秒后,提示音响起:“太好了,那周末见!”
原来,接受善意并非踏入陷阱,而是推开一扇被自己上锁的窗,让阳光重新照进来。

W给我的线圈本,我现在还在继续写。
那些“我还不错”的记录,从最初的刻意寻找,慢慢变得自然:
“地铁上被人踩到,我平静地回‘没关系’,没有再过度道歉。”
“今天主动约了小A一起去食堂,聊得很开心。”
“照镜子时,看到今天的自己,感觉顺眼了不少。”
这些记录,不再是任务。
而是我在每一天里悄然生长的力量,和对自己的温柔确认。
是心理咨询让我明白:
初中那段被霸凌的经历,给我烙下最深印记的不是那些具体的伤害,而是“习得性无助”。
它让我过早地“学会”:无论做什么都无法改变被排斥、被伤害的结果,于是低头、讨好成了我唯一安全的姿势。
这种无助感缠绕着我到大学,甚至更远的未来。
好在,W用那张时间轴,让我看清创伤的位置和边界;
用那个线圈记录本,让我在每一天里重新找到“我还不错”的证据。
这个过程并不轰烈,而是由无数个微小的自我肯定积累起来的。
它缓慢,却真实地重塑着我的内在世界。
如果你也曾经历过孤立或伤害,如果你发现自己仍在无意识地讨好、恐惧冲突、自我攻击、无法坦然接受善意,或是内心总有一个声音在苛责自己不够好……
请相信,这不是你软弱,更不是你的错。
这很可能是“习得性无助”在你生命中留下的印记。
它很顽固,但它也可以被看见、被理解,最终被疗愈。
如果你不知道如何选择咨询师,可以看看这位经验丰富、专业扎实的咨询师——胡少锴。
胡少锴老师是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,从业超10年,服务时长6200+小时,理论和实践经验丰富。
为鼓励求助意愿,胡老师特意开通3个半价咨询名额,原价700元/次的咨询,仅需350元/次。
请你大胆地出发吧
到新的爱和喧嚣中去↓
如果,你也总是一次次陷入习惯性讨好他人、自我否定的漩涡,又想选择更多不同风格的咨询师,不妨试试壹心理的「半价咨询」,找到更合适你的那一位咨询师↓
作者:来访者曙光
编辑:小西
图源:图虫创意、Unsplash
旺源配资-旺源配资官网-什么是股票配资-360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